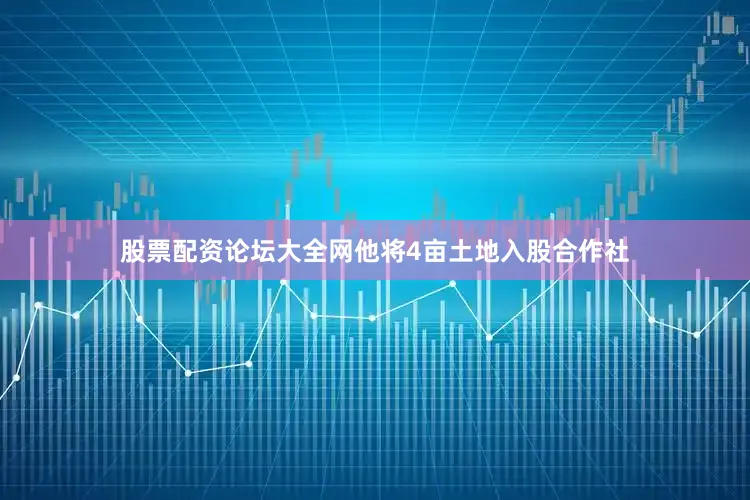*仅供医学专业人士阅读参考

糖尿病合并ASCVD,专家谈残余风险管理。
撰文:一饼
在糖尿病及动脉粥样硬化性疾病(ASCVD)患者的管理中,尽管当前治疗手段已显著降低心血管事件风险,但未来残余风险仍显著存在。在2025美国糖尿病协会(ADA)年会上,三位专家围绕糖尿病合并ASCVD患者残余心血管风险的管理展开深入探讨,从脂质管理、血糖调控及炎症机制等维度带来了最新临床见解与证据。
脂质管理新挑战:LDL达标后,残余风险何去何从?
Mohammed E.Al-Sofiani教授表示对于糖尿病合并ASCVD患者,脂质管理始终是降低心血管风险的核心策略。当胆固醇(LDL-C)达到指南推荐目标后,残余心血管风险仍不容忽视。
▌指南推荐与临床实践的差距
2023年欧洲心脏病学会(ESC)指南明确将LDL-C作为降脂治疗的主要目标,对于极高危患者,推荐LDL-C目标值<55mg/dL。同时,指南建议将非HDL-C<85mg/dL作为次要目标,并对LDL-C达标但甘油三酯(TG)升高的患者推荐使用大剂量二十碳五烯酸乙酯。ADA标准同样强调高强度他汀治疗,要求二级预防中LDL-C降低至少50%且目标值<55mg/dL。
但临床实践中,即使LDL-C达标,患者仍面临显著残余风险。以一例62岁2型糖尿病患者为例,其LDL-C已控制在48mg/dL,但因HDL-C过低(21mg/dL)、TG升高(205mg/dL)及非HDL-C升高(110mg/dL),仍反复发生心血管事件(图1)。这提示我们,仅关注LDL-C远远不够,需采取多维干预策略。

▌LDL-C更低是否更好?
PCSK9抑制剂相关研究(如ODYSSEY和FOURIER试验)显示,将LDL-C进一步降至30mg/dL左右可使心血管事件再降低15%,但仍有85%的残余风险。值得注意的是,即使糖尿病患者LDL-C降至30mg/dL,其残余风险仍高于非糖尿病患者,提示糖尿病本身可能通过独特机制影响脂蛋白代谢[1]。
▌HDL功能比数量更重要
低HDL-C与心血管风险增加相关,但升高HDL-C的干预措施(如烟酸)并未带来临床获益。研究表明,HDL的胆固醇逆转运功能(如HDL的胆固醇流出能力)才是关键。未来可能需要针对HDL功能而非单纯数值进行干预。
▌脂蛋白的危害和潜在价值
他汀治疗后LDL-C达标者中,TG水平仍与心血管事件风险呈正相关。丹麦哥本哈根人群研究发现,当LDL-C达标但非HDL-C或载脂蛋白B(ApoB)升高时,心血管风险显著增加;而若ApoB和非HDL-C达标,即使LDL-C升高,风险也不增加。这提示ApoB和非HDL-C可能是更优的致动脉粥样硬化脂蛋白标志物。
脂蛋白(a)[Lp(a)]是独立于LDL-C的强致动脉粥样硬化因子,但其靶向治疗药物尚未获批。PCSK9抑制剂和烟酸可降低Lp(a)水平,目前两项大型临床试验(HORIZON和OCEAN-A)正探索选择性降低Lp(a)对心血管事件的影响,结果值得期待。
综上,对糖尿病合并ASCVD患者,在LDL-C达标后,应常规评估非HDL-C、TG及Lp(a)。对TG中度升高(135-499mg/dL)者,在他汀基础上加用纯化EPA可进一步降低心血管事件风险。对于极高危患者,可考虑将非HDL-C<85mg/dL作为次级目标,ApoB<80mg/dL作为替代指标。
HbA1c达标≠风险解除,关注血糖变异性与低血糖
传统上,HbA1c是评估血糖控制的金标准,但在糖尿病合并ASCVD患者中,HbA1c达标并不意味着血糖管理的终点。Irl B. Hirsch教授表示持续葡萄糖监测(CGM)揭示了血糖控制的更多维度,为残余风险管理提供了新视角[2]。
约40%-50%的患者存在HbA1c与CGM估算的糖化血红蛋白(GMI)差异>0.5%,22%的患者差异>1%。这种差异可能导致临床决策偏差,如误判血糖控制情况等。高血糖变异性(如血糖波动系数>33%)与氧化应激、炎症激活及心血管事件风险增加相关。长病程糖尿病患者常出现血糖变异性升高,即使HbA1c达标,仍可能存在频繁的高血糖或低血糖波动。低血糖可导致儿茶酚胺释放,引起心率加快、QT间期延长及室性心律失常风险增加,尤其是夜间低血糖与“睡眠中猝死综合征”相关。
基于CGM的个体化血糖管理策略,ADA指南建议,理想情况下低血糖时间应<4%(约1小时/天),但对高龄、合并ASCVD患者,应更严格控制低血糖,目标接近0%。对于血糖变异性高的患者,即使HbA1c达标,也需调整治疗方案以降低波动。对于长病程糖尿病患者,自动化胰岛素输送系统可显著降低血糖波动系数,改善TIR,且不增加低血糖风险。这为复杂病例的血糖管理提供了新工具。
部分患者HbA1c显著高于GMI(>10%),称为“高糖化者”,其微血管并发症风险更高。这类患者可能需要更强化的综合管理,尽管目前缺乏针对性药物,但优化生活方式及控制其他危险因素可能有益。
综上,对糖尿病合并ASCVD患者,尤其是血糖控制不佳或存在并发症者,应常规进行CGM监测,而非仅依赖HbA1c。制定个体化血糖目标:高龄、合并ASCVD者优先避免低血糖,可适当放宽HbA1c目标(如7.0%-7.5%),但需确保TIR>70%且低血糖时间<4%。对于血糖变异性高的患者,考虑使用GLP-1受体激动剂或自动化胰岛素系统,以降低波动并改善心血管结局。
炎症机制新视角:从残余风险到个体化整体风险评估
炎症在动脉粥样硬化发生发展中扮演关键角色,成为糖尿病合并ASCVD患者残余风险的重要驱动因素。Vanita R.Aroda教授提到急性炎症是机体的保护反应,但慢性炎症可促进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形成、进展及破裂。从斑块形成初期的炎症细胞募集,到斑块不稳定时的纤维帽降解,炎症贯穿ASCVD全过程。
高敏C反应蛋白(hs-CRP)是最常用的炎症标志物,其水平升高与肥胖、代谢综合征、糖尿病及ASCVD风险显著相关。此外,白细胞介素-6(IL-6)、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等细胞因子也与ASCVD进展相关。hs-CRP、IL-6等易于检测,适用于人群筛查,但特异性有限。
血管周围脂肪组织(PVAT)炎症可释放细胞因子损伤血管;血管炎症又可反过来影响PVAT表型,导致脂肪细胞功能失调,形成恶性循环。影像学技术(如脂肪衰减指数FAI)可捕捉这种交互作用,冠状动脉计算机断层扫描血管造影(CCTA)可识别高危斑块特征,结合FAI等指标可提高风险预测准确性[3]。
目前抗炎治疗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生活方式干预:地中海饮食可使hs-CRP降低31%,并减少心血管事件;规律运动通过释放肌细胞因子发挥全身抗炎作用。
代谢调控药物:GLP-1受体激动剂(如司美格鲁肽)和SGLT2抑制剂可降低hs-CRP 30%-37%。
特异性抗炎药物:秋水仙碱(0.5mg/d)可降低慢性冠心病患者心血管事件风险,但需警惕骨髓抑制等副作用;靶向IL-1β的坎那单抗(canakinumab)可减少炎症标志物,但因感染风险未获FDA批准。
减重手术:通过减轻肥胖相关炎症显著改善心血管风险。
综上,对于糖尿病合并ASCVD患者,常规检测hs-CRP,>3mg/L时需强化危险因素管理。对高风险患者(如家族性、早发ASCVD),可考虑CCTA评估斑块特征,指导个体化治疗。优先选择具有抗炎作用的代谢调控药物(如GLP-1受体激动剂、SGLT2抑制剂),而非单纯依赖特异性抗炎药物。
总结
糖尿病合并ASCVD患者的残余心血管风险管理已从单一指标控制转向多维度、个体化策略。首先是调节血脂:以LDL-C为核心,兼顾非HDL-C、ApoB及Lp(a),对TG升高者加用纯化EPA。其次是控制血糖:超越HbA1c,借助CGM关注血糖变异性与低血糖,采用个体化目标及新型降糖技术。最后是管理炎症:将炎症视为整体风险的一部分,结合标志物与影像学评估,优先生活方式及代谢调控干预。
参考文献:
[1]Johannesen et al. J Am Coll Cardiol 2021.
[2]Klonoff DC, et,al. J Diabetes Sci Technol. 2023 Sep;17(5):1226-1242.
[3]Antoniadés C et al; Eur Heart Journal;2020;41:748-758.
更多信息,敬请关注医学界 2025ADA会议专栏
责任编辑丨小林
*\"医学界\"力求所发表内容专业、可靠,但不对内容的准确性做出承诺;请相关各方在采用或以此作为决策依据时另行核查。

股票正规杠杆平台,楠希配资,股票讨论交流最大的平台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