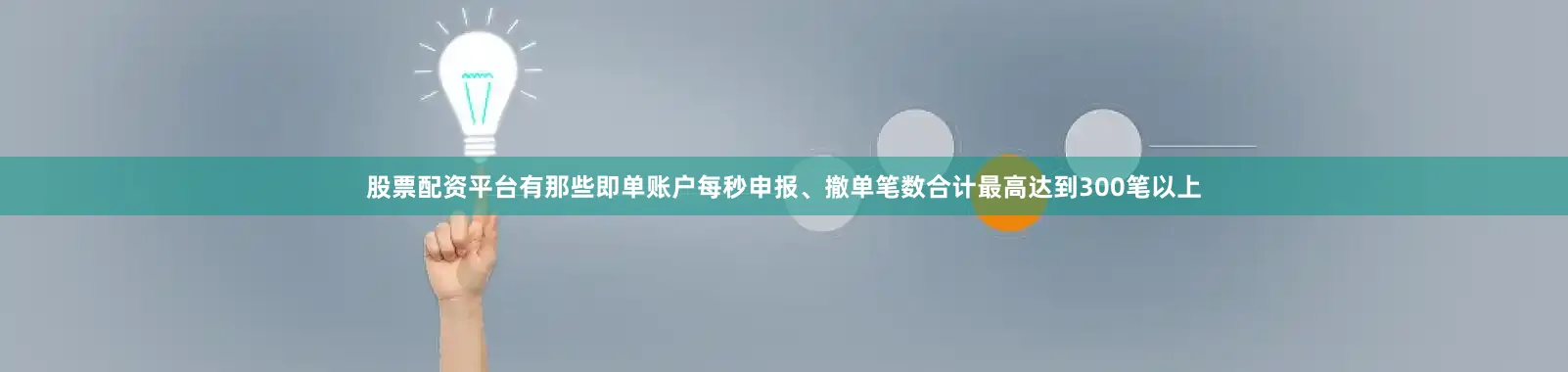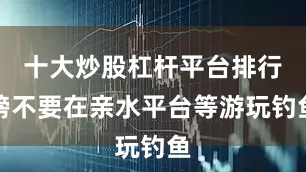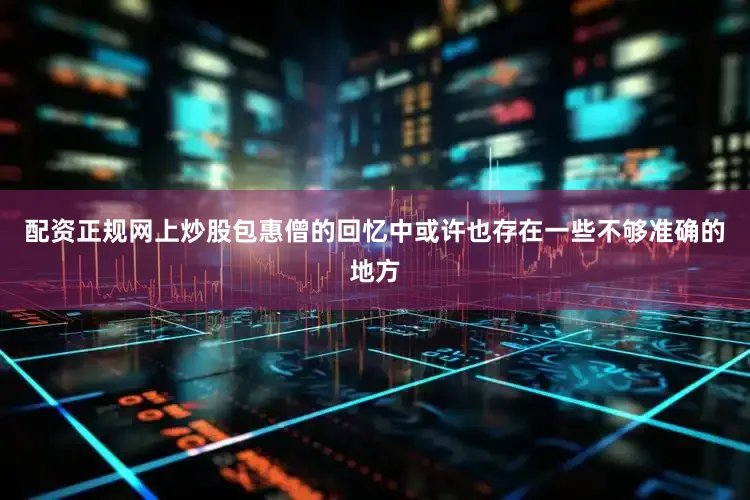
1921至1922年间,陈独秀在上海遭遇了两次被拘捕的经历,以下是其简要概述。
五四运动不久后,陈独秀屡次被捕入狱的经历,无疑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留下了鲜明的印记,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
在彼时,中国已成为各类新兴思潮的试验田,传统的社会架构、思想潮流,乃至政治与文化现状,在各个层面都遭遇了广泛的质疑与挑战。身处这一历史节点,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一批新派知识分子及其追随者,高举“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的旗帜,声势浩大,自然引发了社会保守势力的猜忌与抵制。双方势力的对立与争斗,几乎成为不可避免的趋势。

陈独秀的入狱,实为当时两股势力激烈斗争的阶段性体现。纵然,在南北进步人士及社会团体的共同努力下,加之舆论的强大压力,北洋政府最终不得不在首次拘捕后将他释放。但政府对“新思想”与“新文化”的抵制与打压并未因此减弱,反而愈发加剧,相关措施也迅速增强。1919年8月和次年5月,包括《每周评论》和《新社会》在内的多家刊物接连遭遇查禁。至1922年冬季,当局更是进一步通过了旨在“取缔新思想”的提案,其矛头依旧直指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新派知识分子群体。
在1921至1922年的那段时间里,陈独秀不得不将《新青年》杂志社的编辑部迁往上海,并传闻他以“王旦(坦)甫”为名隐匿身份,行事谨慎。身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局书记的陈独秀,竟然遭遇了两次被捕的经历。首先,他被法租界捕房探员在其住所拘捕,同时被抄没的大量文稿和书籍,案件经过曲折最终以罚金了结。随后,他再次被捕,其住所中的所有文稿、书籍、印刷品,以及印刷用的“纸版”,均被查抄并公然焚毁,用以警示他人,最终同样以罚金作为判决。
两次入狱,幸赖友人积极营救,加之缺乏明确的“定罪”法律依据,陈氏并未遭受长期监禁,不久便被释放。然而,在连续的打压和严厉封禁中,《新青年》的编辑与发行工作遭受严重破坏,最终遭受重创。原本每月出版一期的杂志,在1922年全年仅于7月艰难地出版了第九卷第六号,此后不得不宣布停刊。
褚辅成身份泄露,陈独秀改名亦被捕。
陈独秀被捕及初审
联合通讯社报道,《新青年》杂志的主编,前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陈独秀先生,自去年起担任广东省教育行政委员长一职。近日,因胃病困扰,陈先生请假前往上海就医。星期二(即四月四日)午后两点左右,法国巡捕房派遣数名探捕,前往环龙路渔阳里二号陈先生住所进行搜查,将存放的《新青年》杂志及其他印刷品全部带走。与此同时,陈先生及其夫人,以及前来拜访陈先生的五位友人,一并被带到捕房接受询问。除陈先生夫妇外,其他五位访客褚邵等人随即被交保释放,等候进一步讯问。昨日清晨九时,捕房将陈先生夫妇及涉案人员解送至公堂受审。陈先生聘请了巴和律师出庭辩护;法庭判决陈独秀需缴纳五百两银元作为保释金,并等待两周后的再次审理。其他涉案人员则由原保人担保。

1922年岁末,陈独秀(前排居中左侧)与瞿秋白(后排居中左侧)等同仁齐聚,共赴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
这篇不足二百字的报道,言简意赅,篇幅不长,且刊登位置并不显眼,给人以普通案件报道而非重大政治案件的直观印象。然而,据当时一同被捕的,后于1921年7月受陈独秀委派出席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包惠僧(1894—1979)所述,当时的局势异常凶险——原本在广州潜行归沪进行秘密工作的陈独秀,即便未暴露其真实身份,亦不幸被密探拘捕;在拘留期间,他因与另一位被捕友人的无意识对话,无意中透露了自己的身份,从而被监禁。以下是包惠僧的回忆录:
在上海逗留期间,我某日与周佛海、杨明斋一同拜访了陈独秀先生,柯庆施也加入了我们的行列。恰逢陈先生正在楼上小憩。高君曼邀请我们一同打牌,未料午后时分,前门突然响起敲门声。上海当时通行后门出入,故我对来者表示陈先生不在。他们欲购《新青年》,我告知此地不售,可在大自鸣钟附近购买。周佛海遂先行离开。来者径直入内,指着地上堆放的《新青年》询问。陈独秀穿着拖鞋下楼,见状欲从后门溜走,却遭遇守卫,只得返回前庭。在与来者交谈时,我们气氛略显紧张,但并未透露陈独秀的身份。不久,两辆汽车抵达,我们五人(包括我、杨明斋、柯庆施、高君曼和陈独秀)一同被捕,抵达巡捕房时已近傍晚四点。巡捕房询问了我们的姓名、职业及与陈独秀的关系,我们均报了假名,并留下了指纹,时已五点多。不久,褚辅成、邵力子亦被逮捕。褚辅成发现陈独秀后,急忙拉住他询问情况,导致陈独秀身份暴露。褚辅成和邵力子确认身份后获释。我们随后被送入牢中。陈独秀作为一位有影响力的人物,其被捕在上海引起了轩然大波。第三天,褚辅成、张继等人成功将他保释。陈独秀获释后需随时应召,约20天后再次受审,指控其宣传赤化,最终以《新青年》存在激进言论为由,罚款五千元结案。在马林的干预下,此事得以了结。
从上述近七百字的回忆中我们可以看出,陈独秀被捕当日的情景,宛如一部充满悬念的“谍战剧”,远非报刊报道中所描述的那般轻描淡写,一笔带过。在密探连续数小时的审问和监视下,即便已被押送至巡捕房,陈独秀等人依旧没有透露真实身份,始终以化名与对方周旋。然而,后来一同被捕的褚辅成不慎在对话中透露了“玄机”,这才暴露了他们的真实身份。当然,包惠僧的回忆中或许也存在一些不够准确的地方,例如罚款的具体金额等细节,这些问题将在后续内容中进一步阐述。
既然陈独秀的身份已暴露无遗,邵力子(1882—1967)亦随之被捕,却又迅速获得保释。作为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员,以及《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的主编,邵力子对此事件自是难以置身事外。正因如此,《民国日报》对陈独秀被捕的消息给予了高度关注,连续跟踪报道,所披露的历史信息亦颇为丰富。遵循这一线索,我在《民国日报》中搜集到了大量相关报道,大致可以完整地展现陈独秀从被捕到最终判决的二十余日间的经历。
在1921年10月20日,首次开庭公审的事件引起了广泛关注,《民国日报》和《时事新报》都将此事件作为各自“本埠新闻”栏目的头条。报道指出,法租界密探将陈君夫妇及陆续拜访陈君的邵仲辉、牟有德、杨一生、胡树人、褚慧僧等人一同带回捕房。其中,“邵仲辉”显然是指邵力子(本名闻泰,字仲辉,笔名力子)。那么,接下来的牟、杨、胡、褚等人,他们具体指的是哪些人呢?
包惠僧的回忆中透露,“牟有德”乃是杨明斋的化名,“杨一生”则是包惠僧的别名,“胡树人”实际上指的是柯庆施。然而,“褚慧僧”这个名字却并无实际对应的人物,它可能是报道者在已知“包惠僧”真实姓名的情况下,不自觉地结合了“褚辅成”与“包惠僧”的名字,从而拼凑出了“褚慧僧”这一名称。显然,这种报道中无意泄露的“秘密”,并未引起读者和当局的重视。否则,包惠僧恐怕也难以保全自身。
法租界捕房探长黄金荣,在渔阳里首次将陈独秀成功擒获。
“法捕房对黄金荣等人展开调查,此前曾在法租界环龙路渔阳里二号发现陈独秀家中藏有大量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书籍,遂认定其行为激进。随后,陈独秀及其妻子林氏,以及褚辅成、牟有德、杨一生等人被传唤至法公堂,并被判决交保候审。”
在这篇报道中,虽然遗漏了“褚慧僧”和“胡树人”这两个化名,但陈妻高君曼所使用的化名“林氏”却赫然在目。然而,这篇报道所揭示的历史细节中,更具关键性的信息是明确指出,执行对陈氏等人逮捕行动的,正是“法捕房探目黄金荣”等一众探员。

◆ 黄金荣
此处的“黄金荣”,便是那位与杜月笙、张啸林齐名,被誉为“上海三大亨”的黄金荣(1868—1953)。据考究,黄氏出身贫寒,起初以学徒之身穿梭于洋场之间,随后投身青帮,成为上海南市与法租界交汇地带的一名小有势力的流氓头目。自被法租界当局吸纳至巡捕房,从一名华人探员起步,一路晋升至督察长,他遂然跃升至当地颇具影响力的代表人物。
根据1951年5月20日《文汇报》与《新闻报》所刊登的“黄金荣自白书”,我们得以窥见黄金荣在法租界担任探员时期的生涯点滴。
黄金荣,曾在私塾研读诗书,年幼时便展露了对学问的渴求。十七岁那年,他踏入城隍庙,在其姐夫开设的裱画店里学徒。二十岁学成出师,五年光阴后,他凭借才智考入了前法租界巡捕房,成为一名“包打听”。他最初被分配至大自鸣钟巡捕房工作,那时他正值二十六岁。岁月如梭,他一路晋升,五十岁时荣升为督察长,直至六十岁正式退休。
在黄氏的自述中,提及他初入捕房担任所谓的“包打听”,这正是当年上海人对便衣侦探,即如今的探员的俗称,沪上报刊亦称之为“包探员”;至于“探长”这一职位,也被称作“探目”,正如先前《时事新报》报道中提到的“法捕房探目黄金荣等”所言。若其自述属实,那么黄氏自1894年起便已成为了法租界的华人探员;经过近30年的职业生涯,大约在1921年左右,他晋升为“探长”。正是在这一年,黄氏亲自办理了密捕陈独秀这一重大案件。
《新青年》的出版地历经从上海迁至广州的曲折历程。其中,一则“特别启事”或许导致了陈独秀的被捕。
对于当时的上海市民而言,除了华人探长黄金荣主导的这次抓捕本身便是一大“看点”,陈独秀被捕后,法庭将如何“定罪”,以及律师将如何进行辩护,无疑也是该案件的一大“看点”。
《民国日报》报道称,在首场庭审中,陈氏的辩护律师巴和面对搜查其住所时发现的大量《新青年》杂志,提出了以下解释与辩解之词,以试图为陈氏开脱。
自《新青年》奉旨禁售之后,刊物便转至广州继续发行,并未在法租界地区进行销售。尽管此次捕房在陈家查获,但并未找到确凿证据表明其有销售行为。至于那些订阅尚未到期之读者,陈氏为维护信誉,已准备好等待其来取刊物,这显然与销售行为有所区别。
事实表明,这种辩解最终获得了法庭的认可,否则绝不可能仅以一百元罚金便了结此案。必须承认,巴和律师措辞精准,为陈氏最终能够“清白”获释,提供了坚实的保障。
1921年,《新青年》杂志的发行地是否从上海迁至广州?事实确实如此。正如巴和律师在法庭上所述,存在一份官方文件,提到当年二月禁止销售《新青年》的判决。这份官方禁令一出,该杂志的发行便发生了显著变动。

本社特别启事
因特殊事宜,本社已搬迁至广州城惠爱中昌兴马路第二十六号三楼。今后所有信件,烦请寄送至该地址;至于书报的收发流程,依旧维持上海时期的模式,特此告知。
在本志第八卷第六期的排版工作即将圆满结束之际,稿件不幸遭遇不测,被不慎遗失,而且规定不得在上海进行印刷。因此,本社不得不重新寻找原稿并重新编排,同时将印刷任务迁移至广东。这一切变化导致出版日期无法按期进行。对于众多喜爱阅读的读者朋友们屡次来信询问具体情况,我们深感歉意——或许这应该成为中国向我们表示歉意的时候!
直至1921年9月,也就是陈独秀归国并被拘禁于上海的月份之前,第九卷第五期的《新青年》杂志,其出版发行活动依旧在广州顺利进行,并未触犯上海当局所声称的“禁令”。
然而,当陈氏此次被捕,其位于法租界的居所,恰巧是《新青年》杂志当年在上海出版时的编辑部旧址。这一巧合,自然让捕房探员推测,陈氏此次突然重返上海,恐怕是意图重拾旧业,意图卷土重来。这种推测并非空穴来风;自1919年10月《新青年》杂志从北京迁回上海,其社会影响力便迅速膨胀,令当局深感忧虑,从而不断对其进行干涉和阻挠,直至最终下达“禁印”与“禁售”的严令,意图将其彻底铲除。
新青年社启事
本刊第八卷第一期,定于九月一日与读者见面。编辑团队如故,独秀先生继续负责编辑工作。此后,有关投稿及报刊交换等事宜,请直接联系“上海法界环龙路渔阳里新青年社编辑部”。至于发行相关事务,敬请与“上海法大马路大自鸣钟对面新青年社总发行所”联系。邮费及报价维持不变,但特别号不再额外收费,仅限直接向本社总发行所订阅者享受此优惠。为此,特此提前声明,以消除可能的误解。特此告知。
此则字数不多的公开启事,在8月9日、10日、11日连续三天,于《时事新报》的头版与二版显著位置刊出;尽管连载时间不长,却足以吸引读者目光,确保其知晓度。启事虽未直言停刊三个月的具体原因,然而熟悉《新青年》社重返上海之艰辛境遇的读者,自当明了其中的曲折,无需明说,心照不宣而已。
最终,值得一提的是,为确保上海读者能够及时、安全地获得《新青年》的最新期刊,同时有效规避当局“禁令”可能引发的“违法”风险,陈氏在自粤返沪不久后,便采用了“变通”策略。他将大量在广州印制的期刊寄存于自家住所,并按期妥善封存,以便订阅者能够前来自行取阅。
启事
自本杂志于粤地印制并发行以来,上海的订阅者因缺乏具体邮寄地址,所有订阅报刊均按期封存于法界环龙路渔阳里二号。敬请各位持有效订阅凭证,前往该地址领取。
新青年社
这则“特别启事”的首次见报日期定于1921年10月3日,随后在4日和5日连续刊登。这一发布时间恰巧是陈独秀被捕的前夕。由此推断,或许正是这一份“特别启事”揭露了陈独秀返回上海后新青年社的活动动态,进而透露了他返回上海的行踪。法租界捕房据此完全可以展开监视,甚至采取逮捕措施。
基于前述《包惠僧回忆录》所载现场情景,我们不难推测,当时以华人探长黄金荣为首的法租界巡捕房探员组,应是因察觉到了报纸上登载的那则“特别启事”,才决定对此进行试探并实施抓捕行动。在此,还需特别指出的是,这则“特别启事”连同先前《时事新报》上刊登的启事,以及《新青年》杂志内附印的两则启事,均属于《陈独秀文集》未能收录的“集外文”。除非读者或研究者对《新青年》社从上海迁往广州的历史变迁格外关注,并且频繁翻阅旧报纸并留有心得,否则对此可能知之甚少,甚至未曾察觉。
黄金荣晋升督察员,重归抓捕行动。
陈独秀案已宣判
罚洋一百元
昨日中午十二点半,法国捕房对《新青年》杂志社主任陈独秀的控诉案件,于法公堂作出宣判。陈独秀携同巴和律师一同到庭,静候判决。法副领事以法文宣读判决书,耗时约十分钟。判决内容大致为,虽然查获大量书籍,但并未发现激烈言论。然而,《新青年》杂志被发现违反了之前的法庭指令,因此中西官员共同裁定罚金一百元,此案遂告结案。
陈独秀被捕
陈独秀先生居于法租界环龙路铭德里二号,近日(九月九日)遭到法国总巡捕房特殊部门的西探目长西戴纳,以及督察员黄金荣,华探目程子卿、李友生,包探曹义卿等人的联合逮捕。随后,他们被带至芦家湾总巡捕房,静待公堂审讯。
令人惊讶的是,陈氏再次落网,却并未如上次那般经历曲折,需要周折周旋——这一次,他的羁押时间并未过长;仅仅九日之后(8月18日),便已作出宣判,罚款四百元了结此案。除了罚金数额较上次有所增加之外,并无其他变化。然而,《新青年》杂志在上海的发行与传播却因此遭受重创,正如前文所述,该杂志在1922年全年仅于7月勉强出版了一期(第九卷第六号),之后便不得不宣布停刊。

◆晚年黄金荣。
尽管在次年六月,在瞿秋白等人的大力支持下,《新青年》季刊顽强地冲破重重障碍,在广州得以复刊(虽仅维持四期便宣告停刊),然而,它终究难以与先前每月一期的、堪称“新文化”运动理论阵地的《新青年》杂志相提并论。毕竟,尽管两本刊物名称相同,但无论是在传播的广度和力度上,还是在持续的社会影响力上,二者都存在着明显的差距。
今在上海市档案馆的藏品中,仍保留着一份陈独秀的刑事档案,其中附有一张他被捕时的肖像。这份尘封的档案进一步证实,陈先生于1921年10月及1922年8月两次遭到上海法租界当局的拘捕,原因均系宣传所谓的“过激主义”。这份极具历史价值的档案,与本文所搜集、引用的上海旧报报道相互印证,形成了有力的证据链。
此外,还需特别指出的是,陈独秀在渔阳里首次被捕的次年,即1922年,黄金荣由探长晋升为督察员(同年8月再次参与了对陈独秀的抓捕行动),此后更上一层楼,升至督察长,成为租界华人探员职位的巅峰。至于黄氏为何能如此迅速地晋升,甚至连跳两级,历来说法不一——黄氏曾主办或参与了两次对陈独秀的抓捕,这恐怕是其迅速晋升职级的重要业绩之一。
笔者深信,“黄金荣两捕陈独秀”这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亟需得到更为深入和全面的探讨。对于相关史料档案的开放、挖掘、整理、辨析与研究,仍需我们持续努力,推进相关工作。
“黄金荣拘捕陈独秀”这一震惊一时的悬疑事件,仍亟需更多致力于研究近现代思想史、政治史以及中共早期党史的有志之士,对其进行更加深入细致的挖掘与探究,以便更全面地再现并解析该历史事件的多重细节。
#百度带货夏令营#
股票正规杠杆平台,楠希配资,股票讨论交流最大的平台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